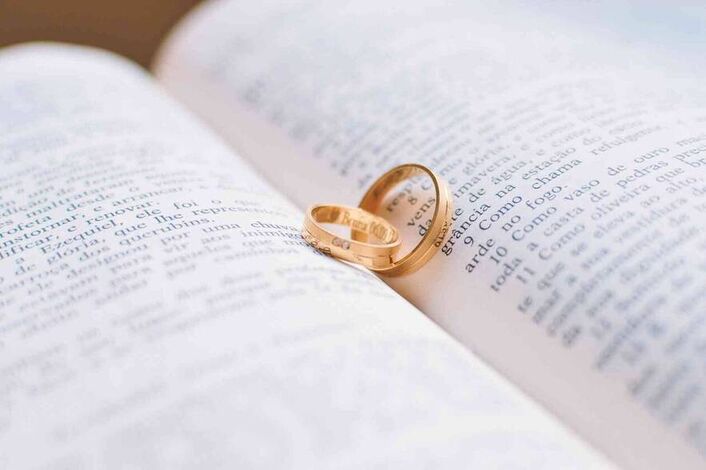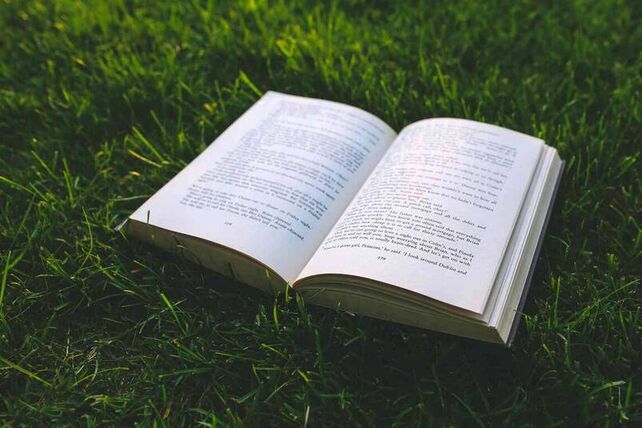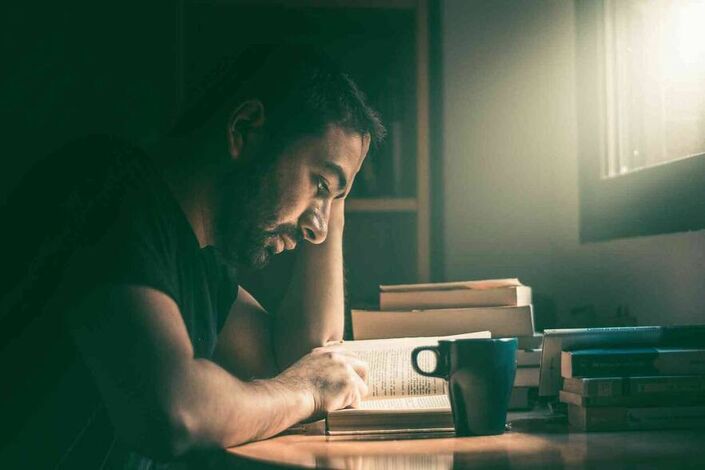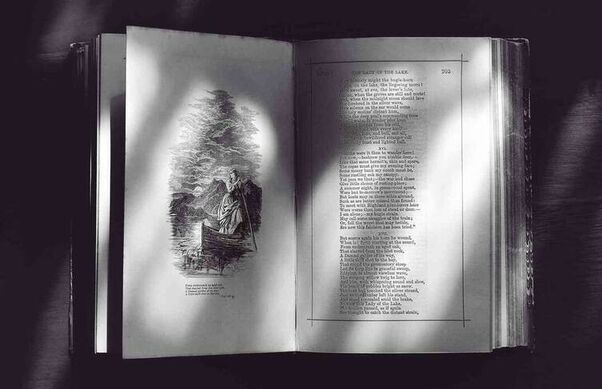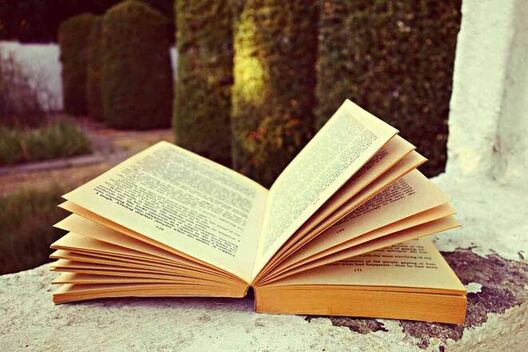本篇文章7806字,读完约20分钟
妹妹在微信圈说她今天包了麻腐饺子。 读了之后,不由得痴呆了。
看到照片上呈漩涡状排列的饺子,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钻入其髓的香味。
几年前,妹妹全家去新疆开了麻辣烫店。 在每天晚上的微信闲聊中,她问我想吃什么,我说想吃麻腐饺子。
睡觉翻微信,妹妹推送的照片是饺子。 附言之,这是她为我匆忙做的,我问她要不要吃。 我不由得心花怒放。
我在福建,她在新疆,这个童年的感觉,即使相隔很远,也还是那么回肠般。
女厨师在武威人心中那就是天经地义的。 因为“武威大汉,吃也没关系”,所以在家里武威男绝对是“爷”。
“你的男人呢? ”然后问。 媳妇们回答说:“没有男人们,出去了。” “有人吗? ”。 媳妇们又回答说:“男人们都到地上去了,都没有。” 这里的“男人”“男人们”是指丈夫。 “男人们”是指家里所有的成年男性。
不知道哪个祖先是从这么优秀的以前传下来的,武威的男人不做饭,拿着餐具也是拿来的。 虽然现在早就变了,但在七十年代以前的农村,男人们做饭会成为邻居们一辈子的笑话,不仅被嘲笑“没出息”,连媳妇们都觉得不好意思。

我们兄弟姐妹很多,吃饭有八十九张嘴。 在家做饭的,先是妈妈,然后是姐姐,再是二妹妹。 妹妹很年轻,每次吃饭都要帮她做饭,她是不可缺少的。 筷子边的碗也是她,但主勺子还轮不到她。 所以我没出门的时候,结果那顿饭是她做的,真的说不出口。

有时候,兄弟姐妹们嘲笑妹妹,故意说“我怎么想不起来你吃了什么饭”。 妹妹一定生气地撅起了嘴。
但是,这句话对于上姐姐、下妹妹,那是气死天了,不闹就鼓励“有碗没筷子”,甚至“碗不喂饭”,一辈子都记得牢牢靠着。 因为自从躺在锅台上,大姐和二姐就再也没离开过厨房。 全家吃她们的饭最多,时间最长。 而且家里人谁都可以经常出门。 勺子主要的东西外出一天,全家人不仅要喝西北风,连猪、羊、狗都讨厌大声喊叫。

我大学毕业了,二妹也结婚了,妹妹终于以勺子为主了。
有一年回家,妹妹拿来碗,郑重地说:“三哥,这顿饭是我做的。 请记住。 我没吃过我做的饭。 ”。
吓了一跳。 就算搜索记忆,也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说了这句没有功绩的话。
但是,这顿饭很好吃。 是麻饺子。 真的是另一种香味。
麻饺子是武威人真正的年关味。
除夕,切肉包饺子,但年夜饭不吃饺子,吃杂菜。 年初一大早吃麻腐饺子。 正月二,吃麻腐饺子。 初中3号亲戚来家里,油果、长面、麻腐饺子依次上来。 “30岁的饺子一开始吃,一年的福拴着弦”“饺子包着麻腐,团圆多很幸福”。 按照武威人的理解,麻腐饺子可能是“麻福饺子”。 新年伊始吃“麻福饺子”,意味着从年到年末福都很密。

小时候没有出远门,只知道麻腐饺子好吃,但最终不知道香到了哪个品级。 离开大学后,我知道了大食堂的味道很累,四海料理也变淡了,麻腐饺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绝香。 在我这里,香谱排单中,武威地道的麻腐饺子可以和淮扬地道的红烧狮子头齐名驱动。

因为做起来很麻烦,所以除了过年以外,平时去麻腐饺子有很重要的意义。
在那个连粥都吃不上的时代,吃麻腐饺子是欺骗娃娃们的愿望,期待新年也常常不能兑现。 在体贴的老人们嘴里,麻腐饺子成了他们最后的主意。 武威词念的一个意思是,心里总是挂在嘴边,但未必能期待。
1973年,奶奶在想断气的几天里,吃了麻腐饺子。 家里很忙,从东向西借了些麻腐饺子。 亲戚和邻居也带着麻腐饺子来探望。 奶奶吃了一点,说:“我满足了一辈子,再也想不出来了。 分给娃娃们吃吧。 ’大人们悄悄地擦眼泪。 在连正常饮食要求都几乎不能实现的时代,你能不悲伤地流泪吗? 那个饺子在嘴里吃起来是什么味道

麻饺子是孩子们对老人的孝敬,也是老人们对子孙的深情。
80年代前的农村,过着公社生活。 公社最大的记忆是不吃而加“两头黑”的劳动。 “两头黑”是指早晚两头看不到太阳。 大人们天不亮就开始下地干活,工作到天黑,一年到头都是这样,所以很少请假。 因为不能休息,也很关心祖母,所以妈妈有时会去看望我们。 武威话系唐宋古音,称母亲父、母为“外爷”、“外婆”。

奶奶在旧社会给大户人家做过饭。 厨艺精湛,特别是麻腐饺子是有名的香气。 每次看到我们,邻居们都笑着说。 “像你这样的小孙子们真的嘴很幸福,我们还能闻到香味。 如果你在镇上开餐厅,保管好所有武威,谁也不敢卖麻腐饺子。 ”。 奶奶哈哈大笑,说:“被你们笑了。 现在吃饭太多了就不能吃饭了,为什么要经营餐厅呢? 娃娃们忘不了这个味道,忘不了我奶奶。 ”。

绝顶的味道,谁能忘记呢?
因为粮食不足,饺子不能全家一起分享,她会单独做一杯给我们吃。 我也只吃过两次。 那种香我以后就没吃过。 武威人称土豆为“山药”。 烤外面老奶奶的山药,炖米粥,都是放在火炕坑里烤的,大部分时候每次都能吃。 半夜才熟,半夜偷偷吃,是让你永远难忘的香味。

很遗憾,祖母这种手艺连母亲都没学到,那味道竟然变成了绝世的味道。
以前我们经常离开外面的奶奶家,但是外面的奶奶死后,变成外面的爷爷经常来看妈妈。 祖父一来,母亲就犹豫不决,偷偷和姐姐商量。 “他又在想那个老人的味道,但我真的做不到。 我该怎么办呢? ”。 外面的爷爷吃了麻腐饺子,慢慢品尝,叹了口气说:“不是那个味道。” 她们不放弃,合计着煎山药,炖米粥,爷爷说:“有那个意思,但没那么香。” 多次来过之后,外面的祖父最终说:“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做出那个味道了! 感叹道:“。

麻腐饺子的香在麻腐上,比麻腐更香。 全家都笑得面红耳赤的那种香更是难得。 因为我常年在外面,所以每次回家,姐妹们总是特意包麻腐饺子,全家都带麻腐饺子吃。 如果碰巧没有麻腐的话,姐妹们会从家里去家里租房子。 如果没有了任何房子,姐妹们会多次聊天。 我当然不介意,但在姐妹们心里那很遗憾,总是遗憾直到我下一次回家。

武威人吃了麻腐饺子,吃得很认真。 如果用麻饺子招待的话,其情分就相当不一般了。
我记得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得过奖。 奖状是一张沾满油的纸。 几天后的晚饭,居然上了麻腐饺子。 姐姐自己拿了一杯,对大家说。 “在今天的饺子里包点钱,看看谁能吃就有福气了。 小心吃,别被人分了钱折了牙。 ’硬币在武威人嘴里被称为‘金子’。

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吃,结果我吃了那两分钟的硬币。 大姐说:“还是上面三个人有福气。 好好学习,能出人头地,那才是你一生的福气,我们也有希望。 ”。
在当时的武威农村,亲人吃饺子分在碗里,交给各自的手。 因为是第一次玩这个图案,所以家人祝福了我。 感受这至诚的祝福,这味道比麻腐饺子的香还要长。
饺子里包钱是友谊。 这友谊远远大于友谊本身。
大姐相亲那天来了很多人,很隆重。 姐夫个子很高,第一次开门,有点腼腆。 那顿饭的主勺子还是姐姐。 热菜中间上了麻腐饺子。 姐夫吃了那笔钱。 但是,由于事先没有证明,姐夫被金子弄坏了牙齿,后面的菜也不能吃了,酒也不能喝了。 妈妈在厨房里小声责备姐姐,姐姐捂住嘴“啊——”地笑了。

那一年,我在高考后,挂着家人的心。 因为没有人知道最终的结果。 但是,没有人出现在我面前。 大姐抱着孩子,我去探望。 她很生气,专门为我包麻腐饺子。
姐姐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吃饺子。 看到我吃了那笔钱,她面面相觑地笑了。 但是,笑了,眼睛里突然流泪,转过头去厨房咽了下去,哭了。
我吃了这钱的味道。 到了大学入学考试的季节,这个味道总是浮想联翩,感慨万分。
大姐出嫁后,二妹为我们做饭,一直延续到结婚的前一天。
当时我在县城念书,周末才回家,后来一直到周末都没怎么回来。 学校伙食不好,总是吃大面包,吃饭,大面包,学习压力很大,我从大胖子变成了高瘦子,从此再也不能胖了。 二妹经常说:“三哥又瘦了,怎么办! 感叹道:“。

每次我回家,二妹总是给我带麻腐饺子。 已经吃得很饱了,二妹还硬塞碗,强迫我吃一碗。 麻饺子很香,但我吃着很呛。
大多数情况下,全家一起吃饺子。 二妹可能忙不过来。 请一个人包一杯吃。 因为做麻腐很麻烦,所以经常吃的话剩下的麻腐就全家吃了,麻腐饺子渐渐成了我的独供。
两个妹妹总是定好我回家的时间,包饺子等着我。 我出门的时候,她总是重复那个问题。 “这周不回来吗? ’包着饺子,如果我没回去,在周末睡觉之前,她总是在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眺望。 这次回家,她一定用柔和的声音说:“你上周为什么没回来? ”我问。 每次,我的心总是道歉。

那年过年,两个妹妹相继吃了麻腐饺子。 爸爸说:“怎么又是饺子? ”。 二妹说:“趁三哥在家,让他多补习一下,看看他怎么瘦。” 武威话的“辅辅”是指补助补助金的意思。 幸运的是她的辅助,让我度过了那个头晕的时期。

自从我大学毕业以来,一年也没回过一次家。 每次我回家,不管第二个妹妹多忙,她嫁之前都会包麻腐饺子给我吃。 那时通信不方便,我突然进门,第二个妹妹抱怨说:“回来了,也不事先说一句话。” 如果碰巧家里没有麻腐,她就急忙去东家西家借,总是在出门前请我吃麻腐饺子。 几十年来,不知有多少家麻腐借来了我这个大嘴巴。

两个妹妹从来不放钱包饺子。 从兰州来福州的那年,我去了两个妹妹家。 进屋的时候,看到第二个妹妹躺在床上,感冒了好几天,起不来。 吃饭的时候,她拿到了麻腐饺子,声音沙哑地说。 “这样一来,就算你再想吃这个,我也不会得到你的”

在那个饺子里,我第一次吃了一张她的钱。
来福州第一次回老家,聊天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能赚钱。 母亲说:“那是个诡计,乐于骗人。 你不看饺子是她们自己带的吗? 那个包着钱的饺子专门放在你的碗里。 不然怎么会那么巧呢? ”。
我问这个饺子是怎么区分的。 母亲说:“我以前也不擅长,但是姐姐相亲的时候终于识破了。 入锅后,饺子先沉入锅底,煮好后浮起来。 其他饺子都浮在水面上。 因为那个饺子包了钱,所以重量很重,不能完全浮起来。 再仔细看看,其他的都是白色,那个饺子在内部能看到隐约的暗色。 反复区分后,取出。 另外,那个饺子一离开热水马上就会变成同样的颜色。 你们不做饭的话,怎么会知道这样的方法? ”。

听了妈妈的话,爸爸几乎一边笑一边流泪,说:“我吃了大半辈子,偶然想到的。”
母亲又说:“我们上辈子没有这个方法。 是她们的女儿们一直在淘气。 意思是想让你摘彩头。 ”。
啊,每个人的成长都不知道有多少彩头默默地支撑着。 每个人都是陌生人,每个人又是彩头的寄件人,无一例外,报酬也很难。
我进屋后,年迈的母亲一直说:“现在谁也不穿鞋,所以我不种大麻。 家里没有麻子腐败,哪家都找不到。 ”。
我去的那天,妈妈还带着麻腐饺子,不知道从哪里想办法。 那香味真的很独特,快要流泪了。 送我的时候,妈妈对爸爸说“还记得明年种大麻吧”。 我几乎流泪了,赶紧转过头去。
途中,我留恋地望着四周。 收割的田园赤裸裸的,那纤细高大的大麻不见了。 过去缝鞋底、搓麻绳、织麻袋都要用大麻皮。 武威是大麻之乡,野都是绿油大麻,一望无际。 告别了穿鞋一样贫穷的日子,结束了大麻栽培的历史。 来到故乡不再种植大麻已经30多年了。 结束了种麻、锺麻、打麻、拔麻、担麻、泽麻、干麻、反麻、山麻的春种秋收,将女性们从四季的剥麻皮、搓麻线、缠麻绳、编鞋底的日夜劳动中解放出来。 种大麻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,但以麻种为调味料的麻腐饺子是世界上最想吃的人的美味。 也许就是所谓的苦美共存。

用于麻饺子的麻腐,是用大麻穗头做成的种子凝固而成的。 姜蘸调味料石臼,武威人称之为“姜窝”。 做麻腐要先在姜窝里把麻籽捣碎。 腊月的23日过去了,姜窝响起一片,那就是家家户户都在做麻腐。
新年的准备工作是极其琐碎的种类的繁忙,只是消磨大量的麻籽,熬一件很细致的工作。 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,所以给我们孩子们分配了工作。 捣姜窝的石槌是大人亲手做的。 我们手小,握不住那个粗石锤,敲了几次都揉不拢手,没观察就跑了。 姐姐很忙,但有时盯着我们看,看到我们逃跑,就会一边追,一边叫,一边哄,一边约。 总之,每年正月吃麻腐饺子,每年12月筑姜窝。 我不记得敲了几次姜窝。 我不记得逃跑后被逮捕了几次。 我不记得吃了多少次麻腐饺子,但那浓重的年关味道我永远忘不了。

几年后再次回到老家,母亲说:“几年前在田地边上种了一些大麻,还收拾了一半的麻籽。 有红白喜事也要用,想要东家,西家纠缠不清,大半都被借走了。 还记得一点,怎么翻也找不到。 ’父亲说:“剩下的东西,也能抓住一些。 她说她舍不得吃,等着你来。 那东西香味很浓,老鼠咬了,虫子吃了,再也存不住了,亲戚庆祝也借了。 ”。 母亲怨恨地说:“这个现在不种了,缺货了,去哪里找呢?”

我进屋后,妈妈马上出去,回来,来回都没空。 我问妈妈在做什么,她只是摇头不说话。 父亲生气地笑了笑,“她没有放弃,到处去借麻腐。 如果有,所有村子里的人,又因为你远道而来,别人能不借给你吗? 我父亲说得对,劝母亲不要吃力。 她答应了又摇摇晃晃地出去了。

我问父亲为什么武威人说“借麻腐”不说“做麻腐”。 父亲说:“天下的人不怕挨饿吗? “要饭”是指乞丐。 吃货方不能说“要”,这是大忌。 口头上说是“借”,其实只是借。 ”。
在我出门之前,妈妈再也没借过麻腐。 妈妈很失望,但那样的绝望无言。
送到十字路口后,母亲说:“再回来的话,一两年前说一句话,我们也准备好了。” 我强烈地笑着说。 “早说,你们要提前种麻籽吗? 儿子到处走,吃东西,吃好东西,腻了。 麻饺子的味道也很一般,高考时胃口大开,早就讨厌了。 因为是你们干的,我很抱歉不吃那个。 ”。

妈妈的眼睛一阵浑浊,然后盯着我的眼仁,看了一会儿,笑了,“你不说实话! 你是怕我老了,种不了麻了。 谁讨厌好东西? 就像你妈的牛奶一样,从吃了第一口开始,这一生永远是最香的。 ”。 我笑了,妈妈也笑了。
我的孩子出生后,带着孩子成了妻子父亲的事件。 妻子的父亲是带孩子的好手,等孩子冷了暖和了他最知道,但他更知道孩子的胃口怎么样了。 的父亲很会做饭,包了20多年厨具,我们也享受了20多年的口福。
预考的几年,学习压力大,孩子胃口不好。 妻子的父亲如何奇怪地插手,是要引起孩子的食欲。 我们很着急。 我妻子的父亲比我们还着急。
一天晚上,妻子的父亲兴奋地说:“今天吃得很好。 饺子一盘也没剩下。 ”。 因为上学很早,所以孩子的饭要早点做,单独吃。 我们到家后就看不见孩子在吃什么了。 反正被他的老人耍着。 老板娘反复唠叨了好几天,高兴的大力士非常罕见。

我问理由,妻子的父亲说:“孩子的事你们一点也不在乎。 做了这两天麻腐饺子,终于吃好了。 ”。 我问从哪里来的麻腐,妻子的父亲说:“我问了很多人,还请熟人从远方送来了麻籽,孩子还是很有食欲的。 ”。
孩子高考前几年,妻子的父亲不断叫人从外地送麻籽。 孩子能够通过中学入学考试、大学入学考试的大关,多亏了老人的无微不至。
孩子上大学后,妻子父亲去了新疆,结束了我们享受口福的时代。 我是没做过饭的“武威大汉”,不得不用勺子。 我不知道有多少好吃的材料半路出家,失去志向,被我糟蹋了。
感到一阵不可思议,萌生了想插手的冲动。 得到了一点麻籽,还让妻子的父亲教她做麻腐的方法,辛苦了一整天。 妻子和孩子到家一吃,风卷云霄,让我感到自豪。
我问为什么这么香,孩子说“麻腐饺子”。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 孩子说:“爷爷给我吃了很多年,我怎么不知道呢?” 听了味道的不同,孩子沉默了。 再追问下去,孩子硬是说:“虽然好吃,但是没有爷爷做的好吃。” 孩子说的是真的。 味道确实不好,不是那个味道。

请告诉姐姐我的电话。 姐姐说:“麻腐使用的是大麻的种子。 大麻油很足,能入味。 你用的是小麻籽,一直很差。 ”。
姐姐又详细地跟我说了做麻腐的方法,“做麻腐在火头上,手头也很重。 头大了不行,小了也不行。 麻腐快没味道了,慢得味道都跑了。 以前家家户户都做,但做出来的味道差别很大。”
我按照姐姐的指导做了猪肉馅。 妻子和孩子怕胖,不肯吃,剩下的都夸我自己吃了。 大众的乐趣少了,有味道的东西终究说不出来。 故乡的味道远不及,儿童的味道更淡了,难以追逐。
妹妹是新疆的麻辣烫店,地方小,人口少,位置偏,同行多,一开始只能维持。 我对她说:“拉舌就拉人。 为什么不推出家乡的麻腐饺子呢? ”妹妹担心地说:“这里外地人很多,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我们家乡的土味。” 我说:“人是五湖四海,但世界之舌谁不喜欢好味道? ”。

于是妹妹在菜单上夹了麻腐饺子。 过了一会儿,食客们争先恐后,越吃越红,妹妹索性打起了“武威麻腐饺子”的招牌。 妹妹说:“果然三哥说得对,天下之舌谁不喜欢香上香? ”我很高兴。
再次到老家时,正好碰上了年三十。 附近傍晚,突然有人卖麻腐,不由得大喜。
卖麻腐的是老人,只剩下桶底。 他问我买多少钱,我说“都想要”。 他笑了:“你没开玩笑吧? 我这点东西看起来不多,还能装几箱。 你家在接待客人方面很重要,也不需要这么多。 ”。 我认真地说:“不是开玩笑,全部都需要。 你的任务是分装,打包,绑好,不要漏,之后要弄清楚钱的数量。 ”。 爷爷惊讶地装在箱子里,一边说:“做这么多事吗? ”我问。 我说:“我回老家过春节,一半和我父母的兄弟姐妹一起吃,另一半带我出国和老婆孩子一起吃,额外分给我的兄弟们,让他们看看世界上最好的香是什么。 这个还多吗? ”他说:“这个可以由武威人做着吃,外地人做不到,给也没用。” “你们的麻籽是从哪里来的? ”。 他说:“去四乡领取。 武威种植大麻的时代很长,总是有人在田边种,留下麻种在家照顾。 这个东西吸引不了虫子,种多了就卖给我们。 ”。 我说:“你们一年到头都在卖吗? ”。 他说:“春节前集中销售,平时很少卖,但首先麻种不好找。” 老人利索,在说话之间打了个包。 一共满了三箱。 付钱的时候,老人说:“你照顾我的生意,我可以去过年了。 你很爽快。 我也很爽快。 收一半的钱。 ”。

我很高兴到家,父亲问,轻蔑地说:“在城里买的吗? 吃不下了,白白扔了钱! ’为什么? 父亲说:“麻腐只有种出纯正的麻种才能闻起来香。 现在麻籽不够了,他们把奸细弄得很光滑,豆腐拌在里面。 看起来完全相似,但八成九是豆腐,没有香味。 信不信由你,我明天就做了。”第二天,弟媳做了两三杯,尝了一下,果然如父亲所言。 不能哀叹内心的古老了。

妈妈抱怨了很久卖麻腐,很遗憾地说:“很遗憾,那笔钱,不是只要求我们这么多,如果真的能让你们再尝一次那个味道,就很划算了。” 过了一会儿,妈妈自言自语地说。 “我知道你想吃麻腐饺子。 你上次说不想吃,是假的,骗了我。 我出生的娃,还不知道你爱哪一个吗? ”。

父母瘸了。 我去的时候,妈妈硬送我回去,说:“麻种不好找,而且我也不行。 你们只要记住那个味道就行了。”我叹息说,“你们会内疚的。
我不由得喉咙哽住,真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。
【作者介绍】邓厚璋,甘肃武威人,1963年出生,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。 生于凉州,学于兰州,住在福州。 文学作品发表在《中华时报》、《网民》及新华网、中华信息网、广播电台等刊物媒体上。 经济社会研究成果发表在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人民文摘》、《国内动态清样》、《经济日报》、《经济参考报》等刊物上。

标题:“郝厚璋:麻腐饺子(散文)”
地址:http://www.5e8e.com/zhjyzx/7689.html